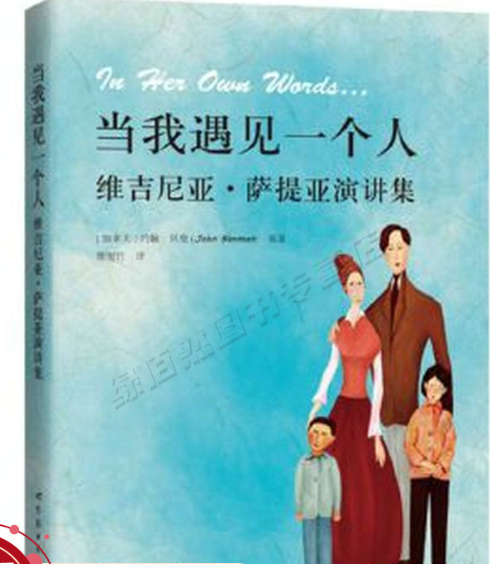维琴尼亚·萨提亚,世界著名家庭治疗大师,她被誉为“家庭治疗的哥伦布”,“每个人的治疗师”,这篇她所著的文章中萨提亚真诚地向读者交流了她个人的专业发展历程,其中的重要观点对于我们理解萨提亚模式或者增进对人的理解和尊重都深有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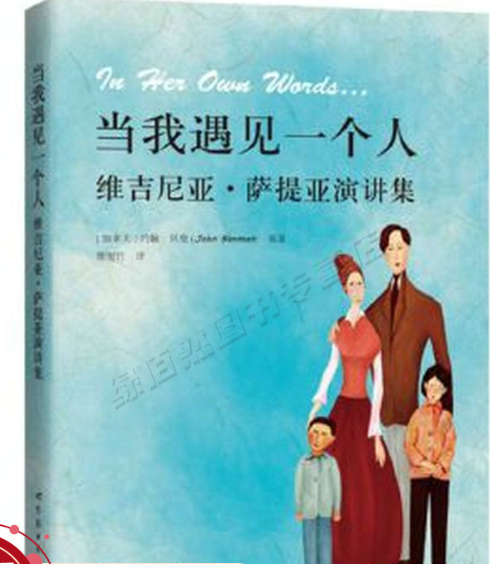
— —文章选自《当我遇见一个人》,约翰.贝曼编著,希望出版社出版。(备注:下文中的“我”即维琴尼亚.萨提亚本人,文章撰于1976年,在她去世前十二年。)在二十五年前,1951年1月,我无意中发现了我的第一个带有“治疗”性质的家庭,一不留神我闯入了后来所谓的“家庭治疗”。那时的我作为一名心理分析治疗师已经有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心理分析治疗让病人发生改变的时间需要很长,但整体来说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才敢于从事私人执业。在“闯入家庭治疗”以前,我有六年的中小学教学经历和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当时,我接手了一名二十四岁的女病人,之前她被诊断为“门诊精神分裂症”。(译者注:指症状较轻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不需要住院治疗,只需定期到门诊复查,这是国外的设置。)在我这里经过大约六个月的隔周一次的治疗疗程后,病人的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就在这时,病人的妈妈给我打电话,威胁说要起诉我使她们母女情感疏远。尽管表面上她在威胁我,但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隐藏在威胁背后的恳求和伤痛。因此,我邀请她一起参加女儿和我的治疗会谈,她马上就接受了邀请。
母亲加入会谈后,病人立即退回到我和她初次见面时的状态。病人所有的成长都从我眼前消失殆尽。我瞬间陷入了怀疑、愤怒、自责等许多情绪的包围之中,直到我的大脑最后告诫我要跳出情绪,只是去观察发生了什么,我才开始冷静下来,不再只是去关注言语的内容,而是试着去观察母女间的非言语信息。我注意到其中有重复的模式在她们之间发生,似乎女儿在与妈妈的互动中采用了与我的互动不同的方式。接下来的观察更让我发现似乎她与妈妈之间的互动模式比与我之间的互动模式更加强大。后来,我从理论上认识到,她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她和妈妈的关系是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而与我则不是。再后来,我意识到除非病人转变为行为的主动发起者,而不仅仅只是回应者,否则她将毫无希望地成为他人行为的受害者。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但是我开始理解对当前互动线索的回应如何影响了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当时我也并不理解,而这些模式反过来又是如何编织成一个系统来满足生存的需要的,但我很清楚自己正在违背心理分析治疗的规则:不要见病人的其他关系人。后来,在与女儿和妈妈一起工作到五或六周的某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关系中可能还有爸爸。我询问她们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过去的那幅病理性的画面只有妈妈,因而是不完整的,所以我邀请了爸爸加入,我再次违反了心理分析治疗的重要规则。爸爸也接受了邀请加入我们的治疗,他的进入使那些模式有了更多的互动,这与我所看到的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情况是一致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所看到的就是后来被贝特森和杰克逊命名为“双重束缚”的现象。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所共有的互动模式。后来,病人的所谓“好哥哥”也加入了会谈,这个家庭的画面终于完整了。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治疗进展得很好。我认为,拯救我并鼓励我继续进行下去的是我忘记了治疗,我只是观察和谈论我所看到的,理论化是后来的事情。当时文献上除了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个案和沙利文的人际理论,绝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我所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任何人在治疗中接待除了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我当时觉得非常孤独。此外,在这段时间我的生计完全依赖私人执业的收入,所以我必须获得“令人满意的客户”(能够支付治疗费用的病人);同时为了职业的声誉,我不能让病人出现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情况。为了我的职业操守,我当然也不能强迫任何病人为我的目标服务。那个年代,心理治疗基本上采用的都是精神分析的方法,我也试图遵守这一状况。此外,这也是我治疗的唯一途径,我当时拥有的唯一工具就是精神分析。此后,我开始逐渐邀请其他病人的家庭成员加入到治疗会谈中,观察是否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对于观察到的这些现象,我还没有完全理解,另外也不知道如何去创造性地解决。后来我从经验中发明了一个新的治疗工具,我称之为“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family life fact chronology)。当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我会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事件中的基本事实,即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对谁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并不是社会史,而是家庭编年史。我侧重记录那些具有发展意义的事件和创伤性的故事,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只是简单地认为,如果我列出家庭中的父母从出生到现在每年发生的事件,就能够获得一些有关这个家庭发展完整的感受。这个工具让我有机会了解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对“编年史”中的事件是如何体验的。
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少有家庭成员真正了解事实,他们彼此的观点也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事实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也许“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谈论的是过去的事情,但事实上却是在构建当前家庭的现实情境。家庭成员间可以通过“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开始彼此的沟通,包括添加、纠正、告知和正视各种信息。此外,这一工具也有助于我理解他们过去的情况并获得当前家庭纠结的各种力量的线索,而正是这些力量提供了家庭发展的动力。“家庭编年史”成为一种按时间和地点排列家庭事件的可信赖的工具。我试图将这些家庭中发生的事件呈现给冒险而来的家庭,对于家庭中所发生的不管是正性还是负性的事件我都会给予同等的关注,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让家庭成员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个人对互动信息的回应方式上。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编年史对我最大的回报就是它被证明是一种可以信赖和易于理解的工具,它能真正地揭示当前家庭的互动方式。我开始真正了解家庭中每个人对其他人的想象和期待,而事实上这些在他们之间从未被澄清过。这一点就是我现在的沟通理论的基础。在完成了几百个案例后,我开始看到家庭中各种系统的出现和影响,由此我的信心倍增。这一工具也成为我现在帮助个体做家庭重塑(我发展的另外一个工具)前做准备的基础。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在生命早期所获得的知觉常常成为他衡量所处世界以及其他人的标准,似乎他仍然生活在儿时的情境中。这并不一定是个新观点,我称其为“过去的学习经验”。我有所创新的部分是我能够帮助人们在觉得安全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和理解他实际所处的情境,而不再继续停留在早年的感觉水平。顺便说一下,我大部分的治疗工具都是在偶然事件或根据某一刻的治疗需要形成的。例如,模拟家庭工具是在1962年到1963年期间我在科罗拉多州福利大会进行家庭治疗演示时发明的。当时因为人们忘记了安排一个我所要工作的家庭,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努力克服随之而来的恐慌,我告诉自己:“好的,维吉尼亚,如果你对家庭系统是如此熟悉,你应该能够进行模拟家庭演示。”这是我头脑中突然冒出的想法。我尝试着这样去做,后来证明它不仅效果显著,而且成为了我一直使用的工具。
沟通姿态是某一天我正在思考我所遇到的各种沟通应对方式时形成的。我头脑中自发地出现四种不同的行为应对方式,这与我多年来观察到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四种行为似乎都是为了生存,但表现出这些行为的人们却对此没有觉察。现在我相信一个人在内心感受和外部表现之间可能并不相同,我称之为不一致。这并不是新观点,但是我在其中增加了一个生动的身体姿势画面。由于我认为身体姿势比言语更有效、更清晰,所以我发明了所谓的沟通姿态。我已经发现,特定类型的语言会伴随着特定类型的身体姿势和情感。我只是把它们加以扩展,变得更加夸张化。例如,对一个抑郁的人,我让他以一个笨拙的失去平衡的姿势跪着,头向上看,肩膀弓着似乎乞求某人的拯救,似乎这才是他生存下去的理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姿势雕塑出互动的方式,表达了人际间的疏远和地位的高低。我也能够看到人们如何同时表达两种信息,例如“过来”和“走开”,我称这样的形式为家庭雕塑。这一工具在使用中被不断发展,现已成为引发觉察的有力工具。1964年,伊沙兰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发现了那些被统称为情感领域的知识。在那里我遇到了那些终身对此进行研究的人们,至此我才意识到在治疗领域我所观察到的只是一部分,而其他一些人已经探索得更深入了。关于自尊的概念一直是我工作的重点。现在对我来说,似乎自尊与我们的灵魂和精神(自己神圣的部分)的密切程度就如同它与我们的身体、情绪、智力、我你关系的体验及信念的相关程度一样。于是,我似乎开始明白,无论何时,当我们试图开始帮助其他人时,就必须对人类的灵魂带着深深的欣赏。二十年前我非常小心地避免谈论、甚至提及灵魂,因为那是组织严谨的宗教领地,在心理治疗的“科学”中尚没有它的位置。
我相信我们正在开始突破性地进入一个完整的新的精神世界。我发现,获得自我价值感的人是不需要依靠别人而不劳而获的。他们明白,他们的生存更多建立在他们有能力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主宰着自己的反应和行为。他们坚信,生命是一个发展过程,总是能够改变,而且他们有勇气愿意冒险。我现在认为,治疗师的工作就是帮助来访者形成这些品质。我也清楚如何改变人们的互动系统使它朝向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是相反的方向迈进。随着我不断的成长,我已经拥有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存在某些可以被称作生命力或普遍精神的东西。我知道这种力量包含了许多方面,它们强有力地塑造着人类行为。对我来说它有点像电流,总是在那里,等着人们去确认并学会如何使用它以实现有益的目标,这大概就是被称之为是精神力量的东西、某些我们体验到的类似于氛围的东西。常常有一些观点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像一个发电单位,是我们的能量发动器,利用电力的大小主要由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程度和感受所控制。我知道当我处于低自尊状态时,我的能量就会低,并且常常指向错误的方向,即大多数时候都是反对自己的。对我来说,这些体验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前进方向。不过,很多时候,我认为我很难自己帮助自己,因为涌现出这么多的体验,我需要强迫自己才能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观察和探索。作为家庭治疗师,我现在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地促进每个家庭成员自我的发展,并在家庭、社会机构以及整个世界中建立滋养型的人际关系。这显然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作为治疗师或老师,我发现,如果要很好地帮助人们开始去冒险改变和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我自身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否则在家庭治疗和培训中都不可能产生太好的效果。因此,我自己继续前行的方向就是观察和体验所有能够开启新蓝图的事情。正是在那条路上,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将随着我面前打开的蓝图而继续延伸。